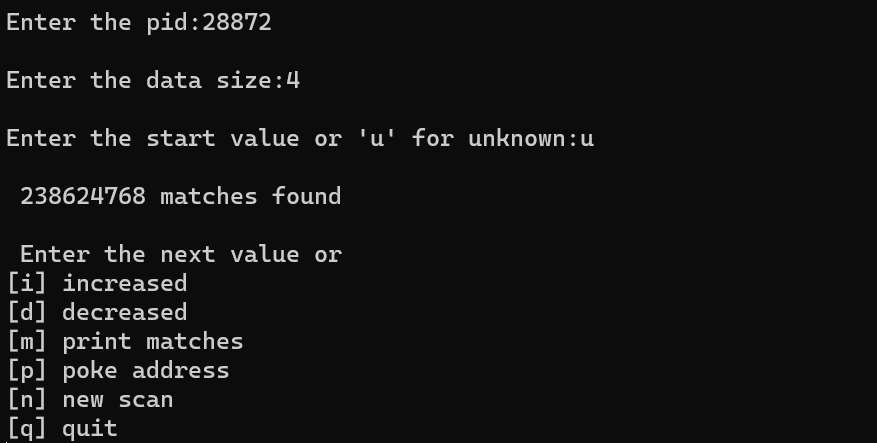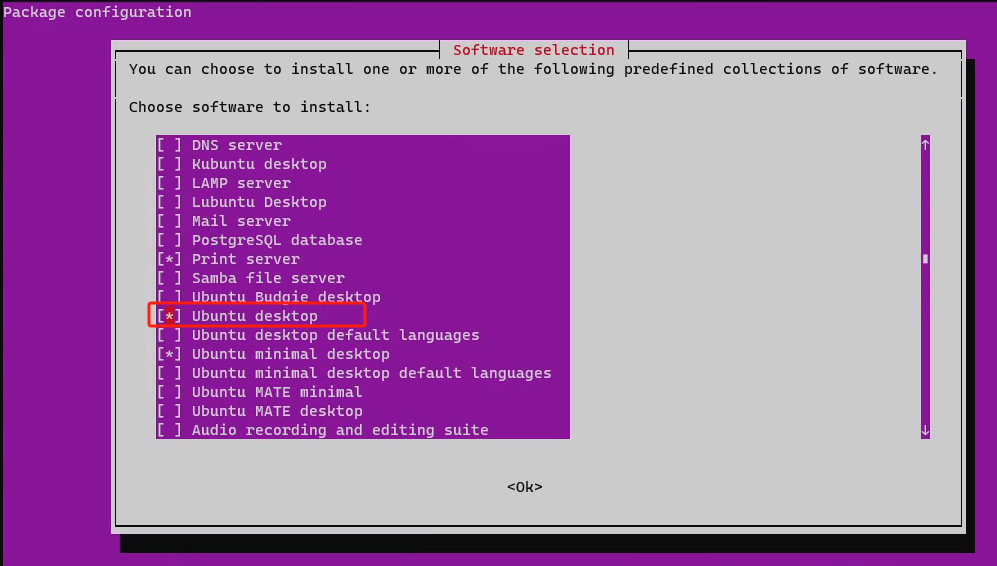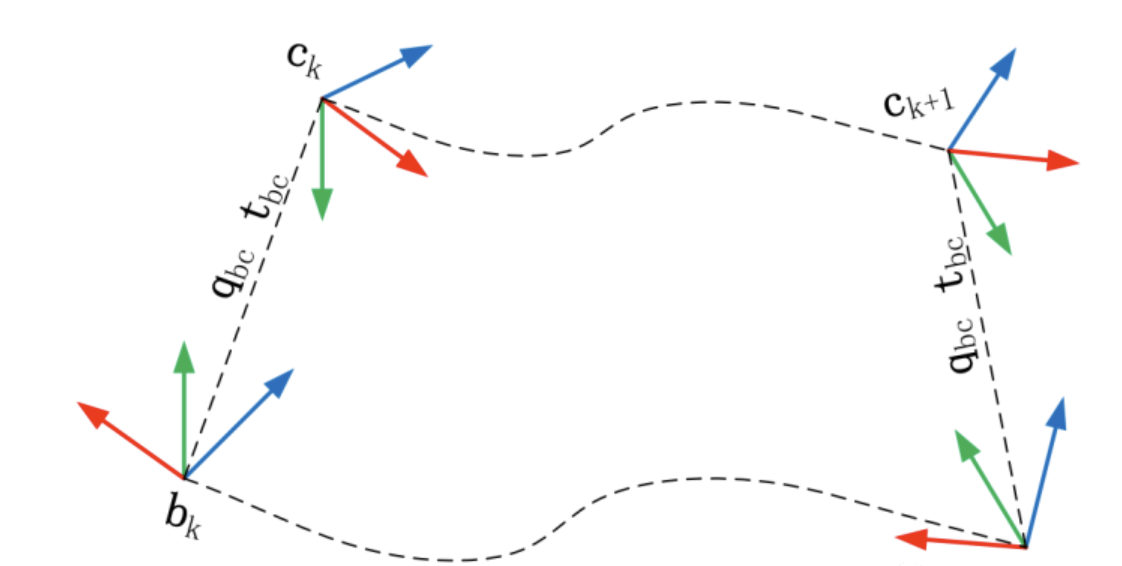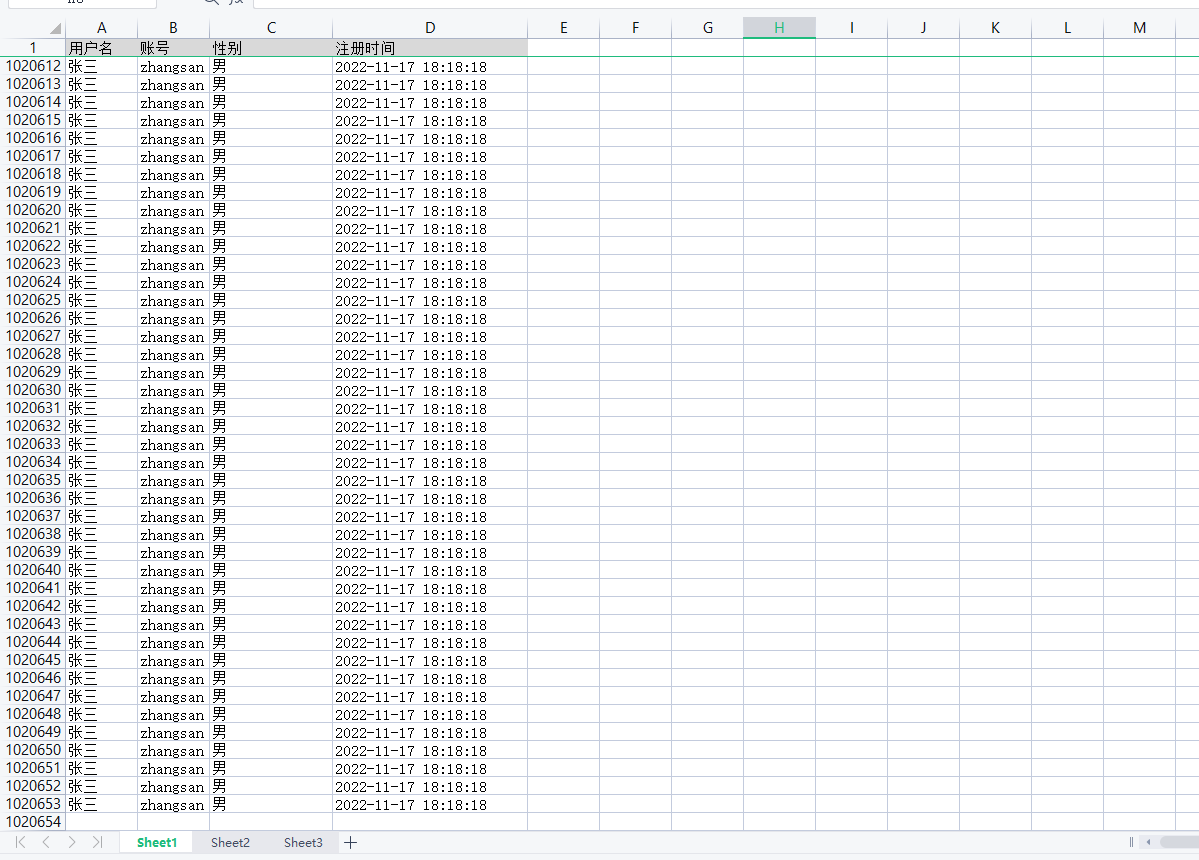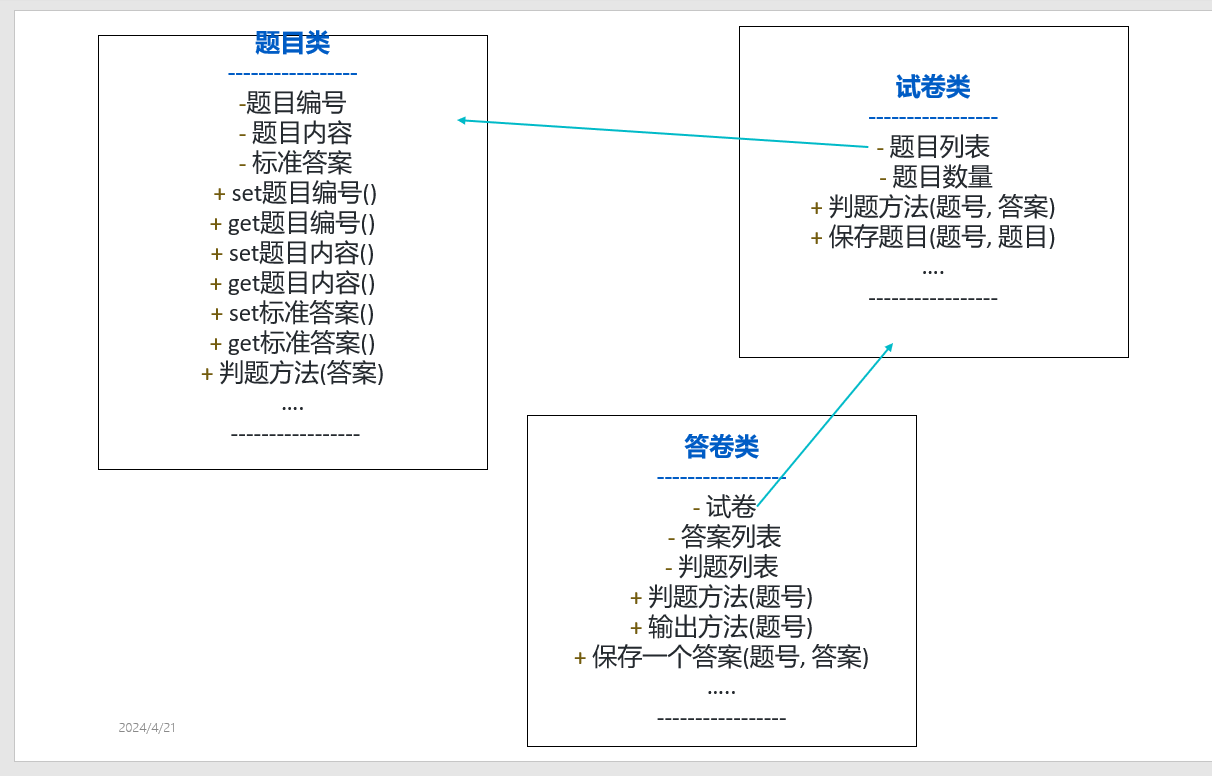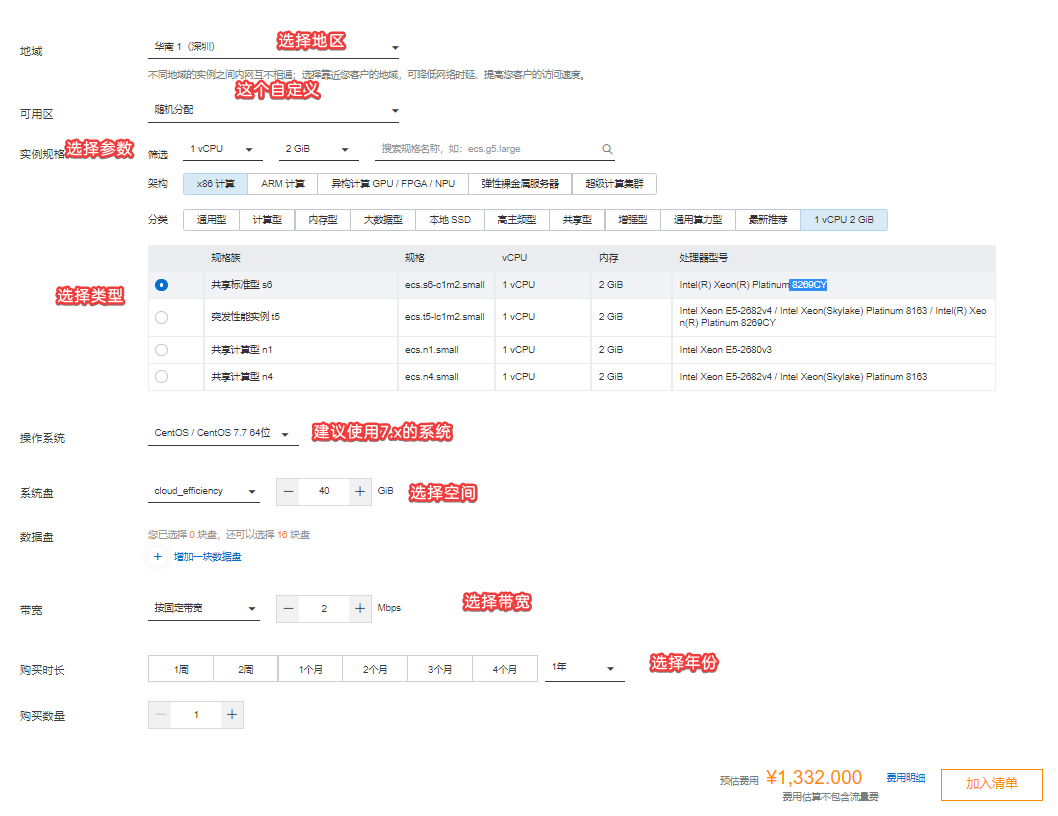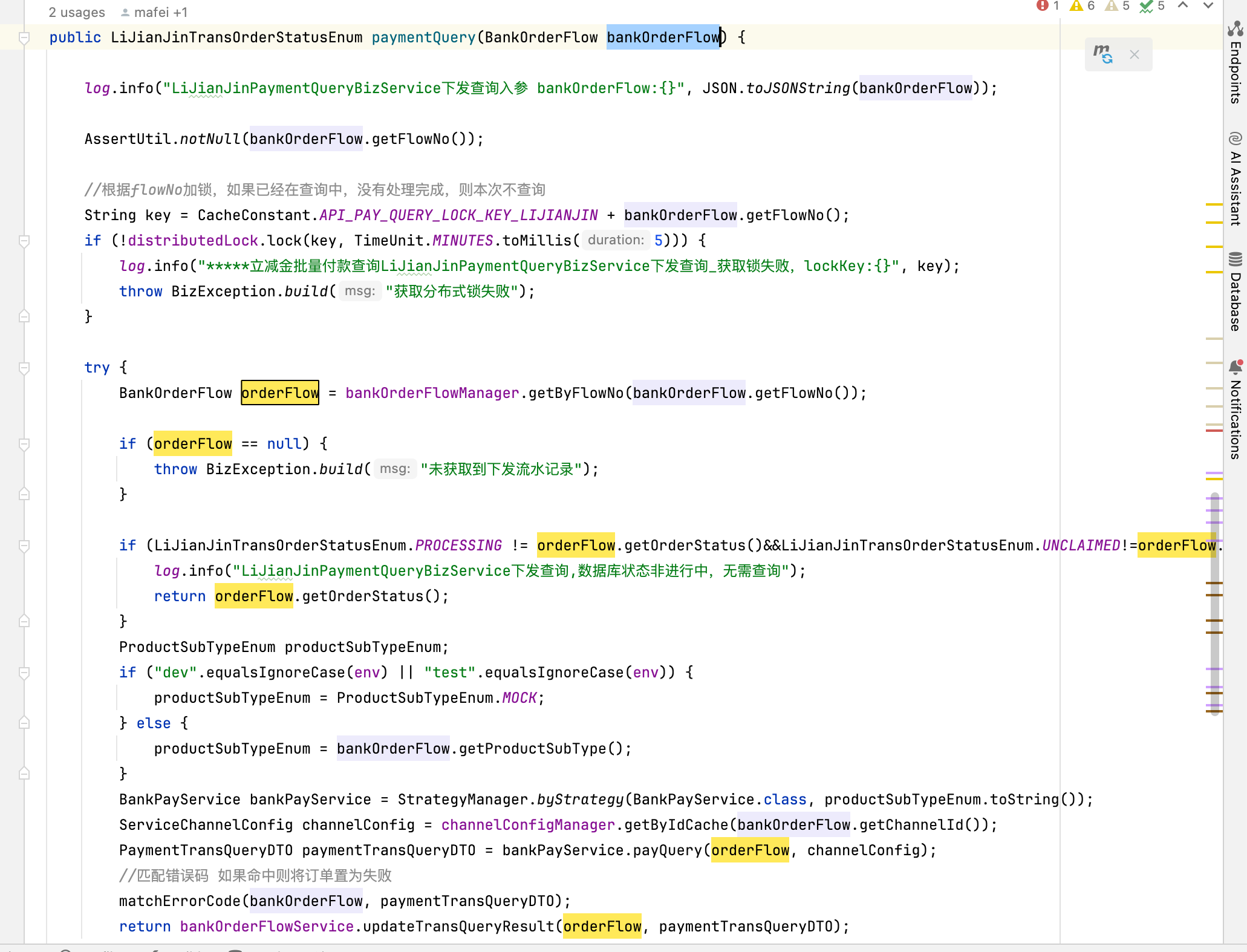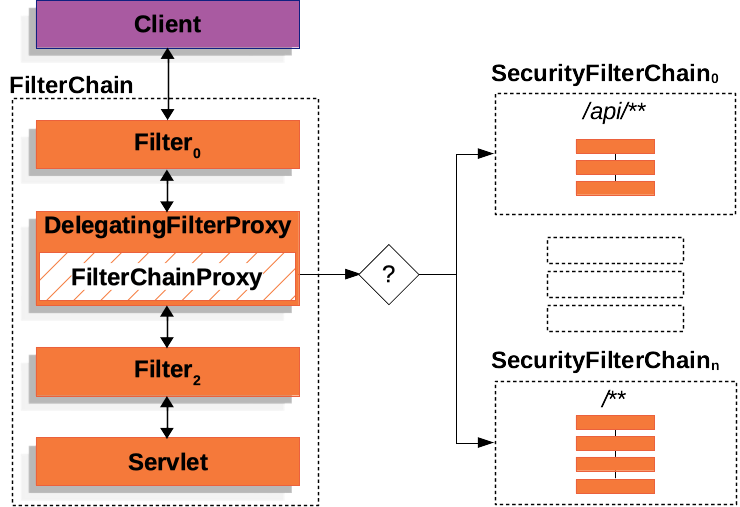大雪,废墟和明天见
文/轩先生
(一)
在许多年后,太阳直射线慢慢从赤道移到北回归线,外面阳光日益温暖,冬季的坚冰慢慢融化,化作一股激流从青藏高原奔腾而下,涌入长江、黄河,冲进每一条支流小溪,树上开始抽出了嫩嫩的树叶,这股力量冲进水力发电站,通过电缆成为万家灯火。
但当前,街道上的气氛冷得像一块泛蓝的坚冰,湖水泛起的涟漪搅散黄昏的倒映,月亮带着黑夜徐徐不行而来,口罩也要让你透不过气来。
我开着车回家,马路上只剩下一辆没有乘客的公交和几辆发呆的出租车,我突然发现这样沉寂的夜是那么熟悉,坐在副驾驶的爸爸缓缓地点了一根烟,略带兴奋地冲着空无一人的公交车挥了挥手:“嘿,还没下班呢,路灯都下班了!新年快乐司机师傅!”
天空开始下起雪,父亲打开了音响并开到最大声,放着十年前的,不对,二十年前的音乐,在这寂静的马路上肆意哼唱。
空无一人的红绿灯下我有点恍惚。我摇下窗户,任由冷风灌了进来,我说:“爸,你还记得上一次这样下雪是什么时候吗。”父亲用夹着烟的手揉了揉鼻子,笑了:“我怎么不记得,那年你还是个小屁孩,现在你都会开车了,哈哈哈哈。”说完他又高兴地哼了起来,“真快啊!时间!”
2008年年初,那是我第一次见这么高的雪堆,比八岁的我整整高出了两个头,院子里的南方孩子都兴奋极了。整个大院都被一层厚厚的积雪覆盖,大人们为了铲出一条能行车的路,艰难地用竹扫把一点一点把雪从路中间扫了出来。
平日里老实巴交的环卫工仿佛神兵天降,不知道从哪里变出来一把多年没用的铲子,将整片路清理干净。光是扫开一条勉强够小轿车进出的干净路,就花了一个上午。
我偷偷拿了爸爸用来清理煤灰的耙子在院子里到处铲雪,然后攒成一个压实的雪球,在那个比我们所有孩子都高的雪堆旁边做了一个简陋的雪人,男生给它装上眼睛、鼻子、耳朵、眉毛,女生就给它穿上手套,带上帽子。
大人们就站在我们后面,用相机给我们每个人都拍照,笑呵呵地说:“今年这雪真他妈爽,就是得这样,狂下雪,哈哈哈!”
(二)
2008年年初,一场历史罕见的特大冰雪灾害开始袭击中国南部,很多人都印象深刻。在接下来的一个月时间里,灾情波及半个中国,湖南雪灾尤为严重。--红网记者报道
“咔嚓”一声巨响,我们知道又有一棵树倒下了。小区里很多百年老树,我爷爷说他年轻的时候曾亲眼看到它们落户在这个大院。有些树不堪大雪结冰的重压,加上冰灾期间几乎能卷走人的大风,最后以一种不太体面的方式躺倒在公园、花坛、甚至直接躺倒在房子上。
大人们围坐在小区的花坛边,中间是一个变了形的不锈钢脸盆,里面装着还包裹着冰块的树枝、树干或者树叶。大人们就围坐在火堆旁,看着这些百年老树的遗体吐出火舌发呆,看上去忧伤不已。
这样一片属于冰雪的废墟里,孩子们是天生的冒险家。那年一棵双手没法合抱的苍天大树砸穿了我家的阳台,小孩子们可以踩着树皮着力爬上爬下,就这样许多好动的孩子就成为了我家的常客,爸爸说爬上爬下的很危险,可我总是偷偷地从阳台的树上滑下去,又爬上来,又滑下去。
爸爸后来因为担心,费了好大劲把爷爷奶奶接了过来一家人住在一起。爷爷看到这棵树之后眼睛眯成了一条缝,愣了半响,飘出来一句:“是棵好树。”
倒塌的树木和围墙天然地围成了一个帐篷形状,而入口又刚好只有行动自由的“小小冒险家”们才可以穿梭自如。在这样小小的方寸之地展开我们的冒险,小孩子们围在一起宣誓做永远最好的朋友,不论发生什么也绝对不会背弃伙伴。
“小小冒险家”都会把自己最不想让爸妈看到的东西藏在这块营地里,有的人把自己的日记藏在这里,有的人把自己没及格的语文试卷偷偷藏在这里,我把偷来的阳台钥匙偷偷藏在营地的泥巴下面。我们在营地里开心的讨论着新上映的动画片,猜测接下去的剧情,我至今仍然记得那天我和一个女生争论黑小虎到底是好人还是坏人而生气,一天没理对方。
小孩子嘛忘性大,天一亮,我们就都忘了。
最开心的是每次出外采购的志愿者越过滑溜的冰面,从外面带来救助的物资的时候,不仅会有些蜡烛、打火机、粮食、肉这类必需物资,人家心疼孩子吃不上好零食,常常会带来一些高热量的糖果,很多都是我们没见过的外国牌子,一袋袋的,分给我们这些小飞侠们。
也许是真的馋了吧,下暴雪的日子里因为出入不便,除了必要的进食几乎什么食物都找不到,吃的我们眉开眼笑的。
那时大人们都坐在火盆边上发呆,一边咒骂着这无端的天气,另一边则拿起各自家里的瓜子花生坐在一起开心的聊起过去的光景,而我们都盼着这场大雪可以下呀下,一直这样下着就可以不用上课,不用写作业了。即使没有电视看,我们也可以爬一整天树,白天可以就着阳光看漫画和故事书,晚上可以在火炉旁听大人们聊过去的事。
(三)
雪不会一直飘下去,就像我们不会一直这样玩闹下去。
铲雪车轰隆隆地开到大院里,大批志愿者带着长长的棍棒打落树上的冰片,掉落的树枝也堆积在原来我们称之为营地的地方。太阳出来了,雪彻底化开之后,那些散落的枝、整根断裂的百年老树、连同我们的秘密基地,就这样被付之一炬,成为这场灾难最后剩下的一地鸡毛。
最后一天我们几个小伙伴站在吞吐火舌的营地旁,有的哭,有的笑,有的又哭又笑。我记不清自己是什么表情了,我只记得那火有些温暖。
后来很多年,我再也没有回去。我听说营地早已没有了它的痕迹,有人挖了挖原营地下的土,却没找到那串钥匙。望着满地巨大的树桩,总觉得那里好像有好多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