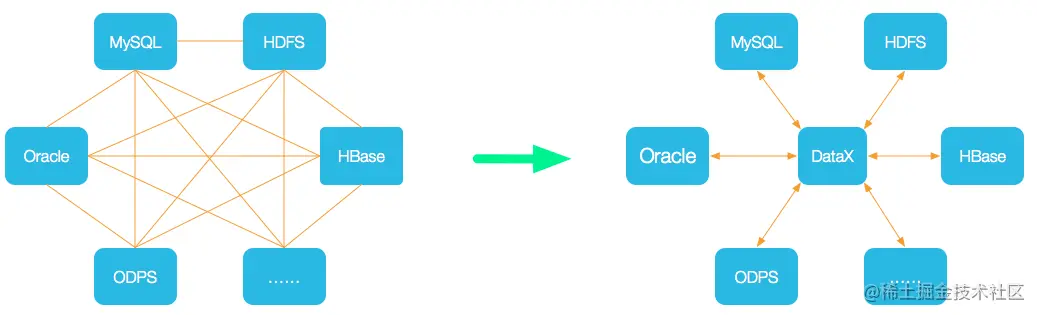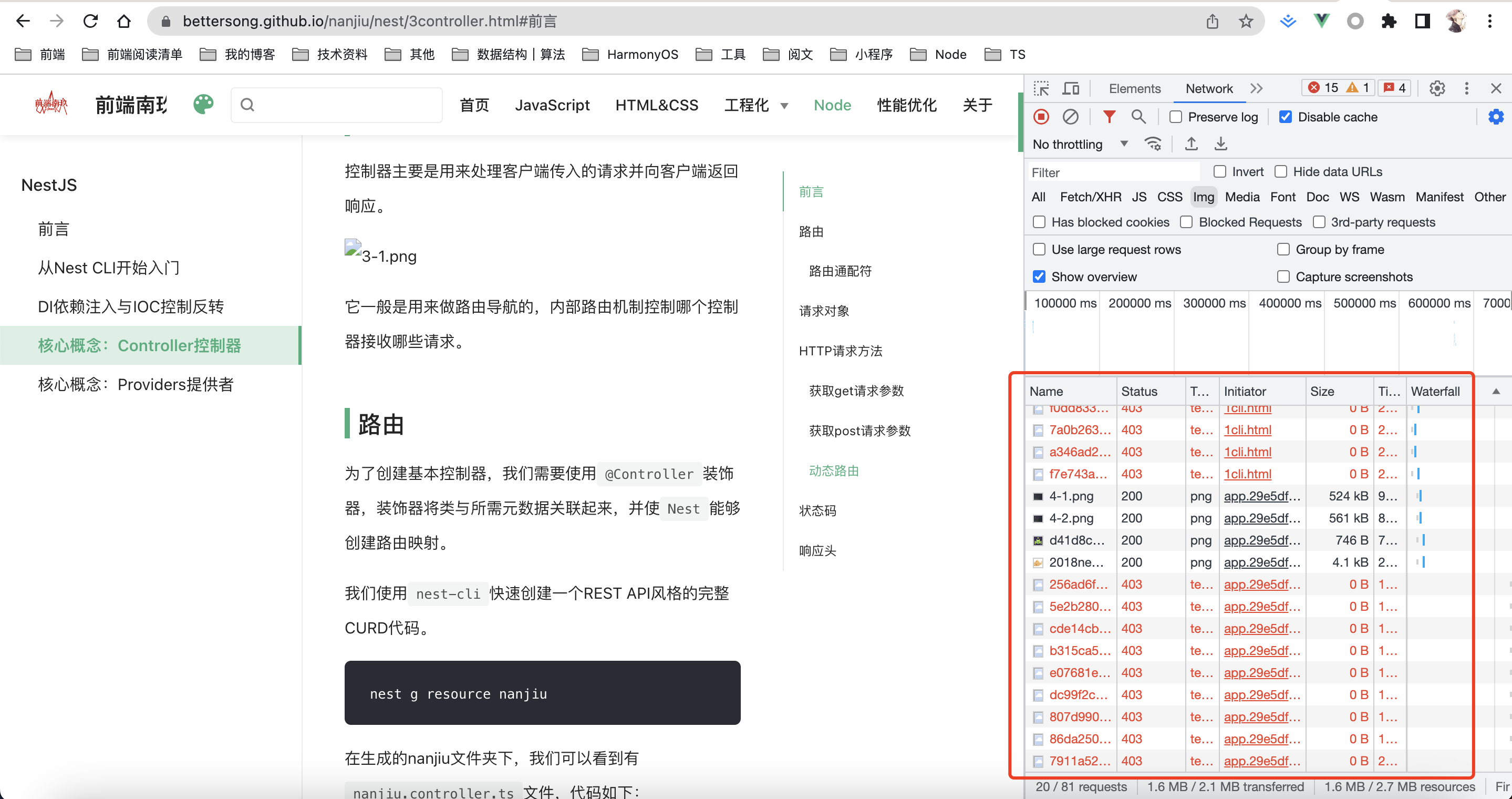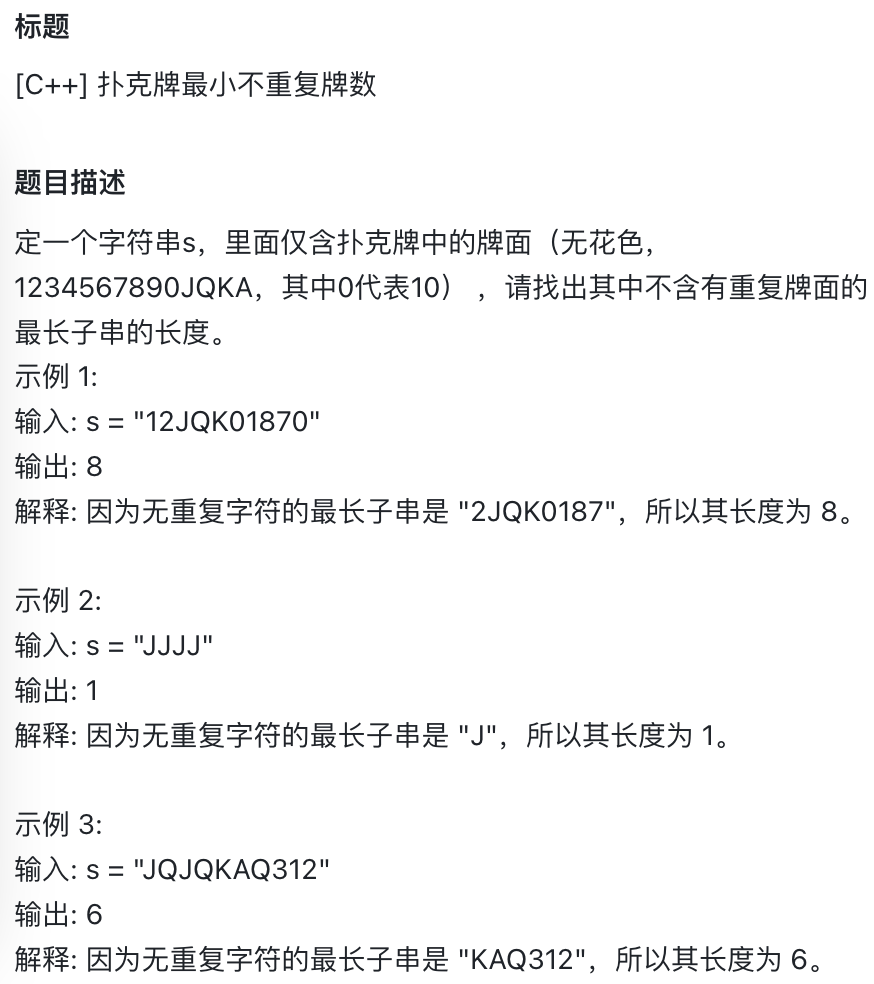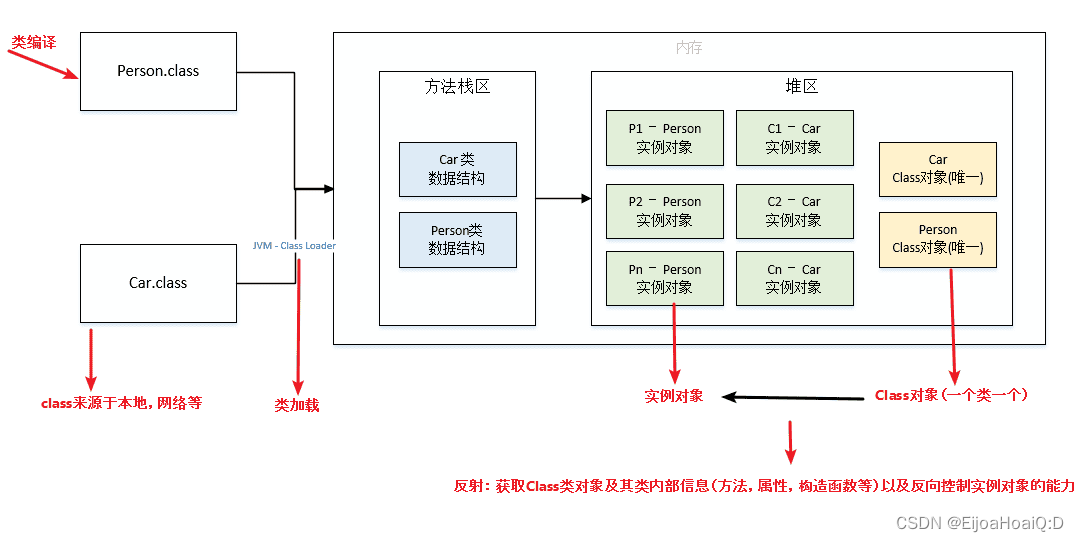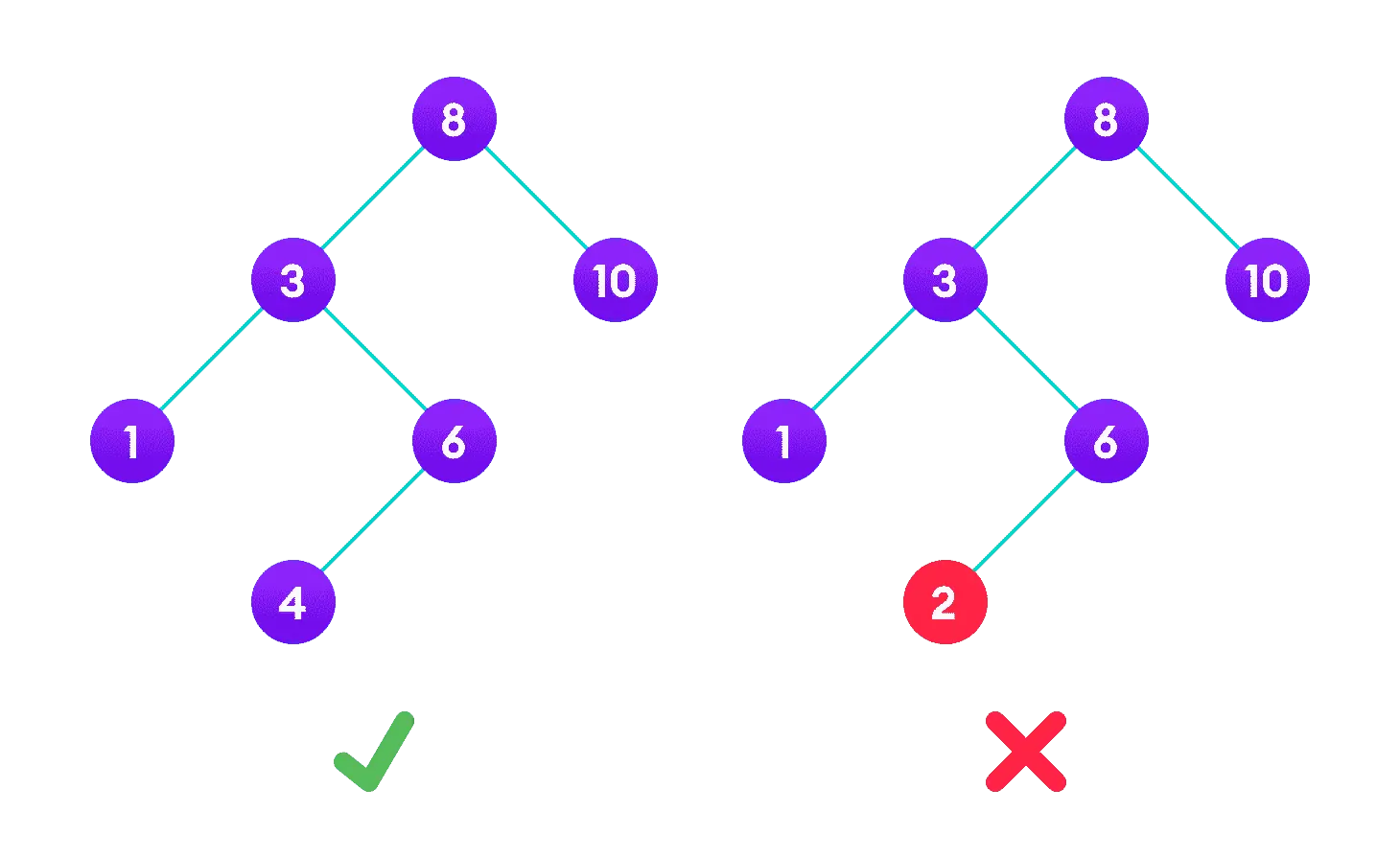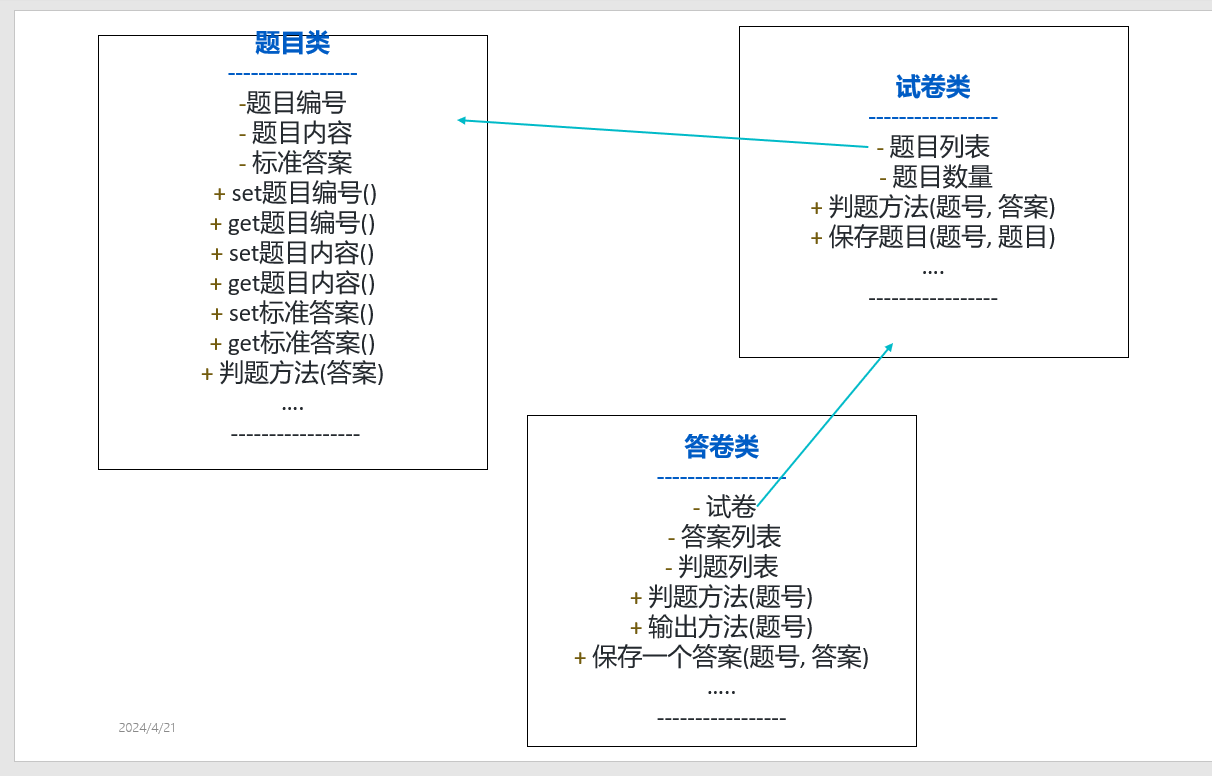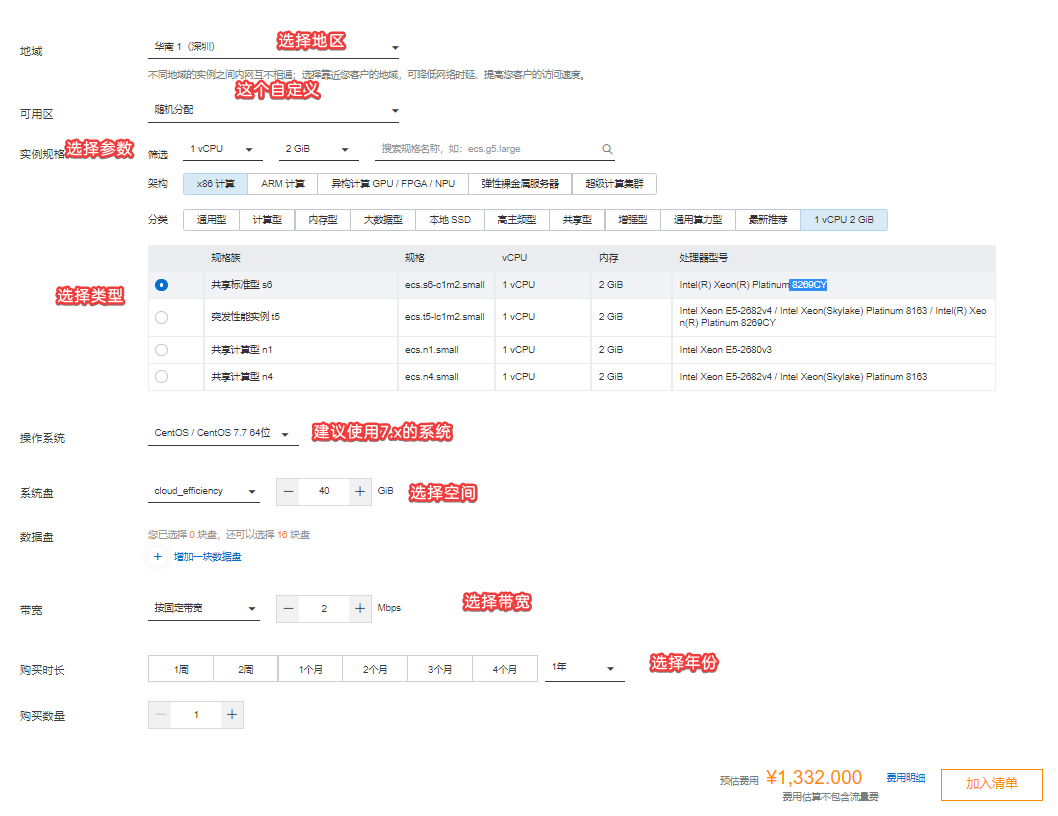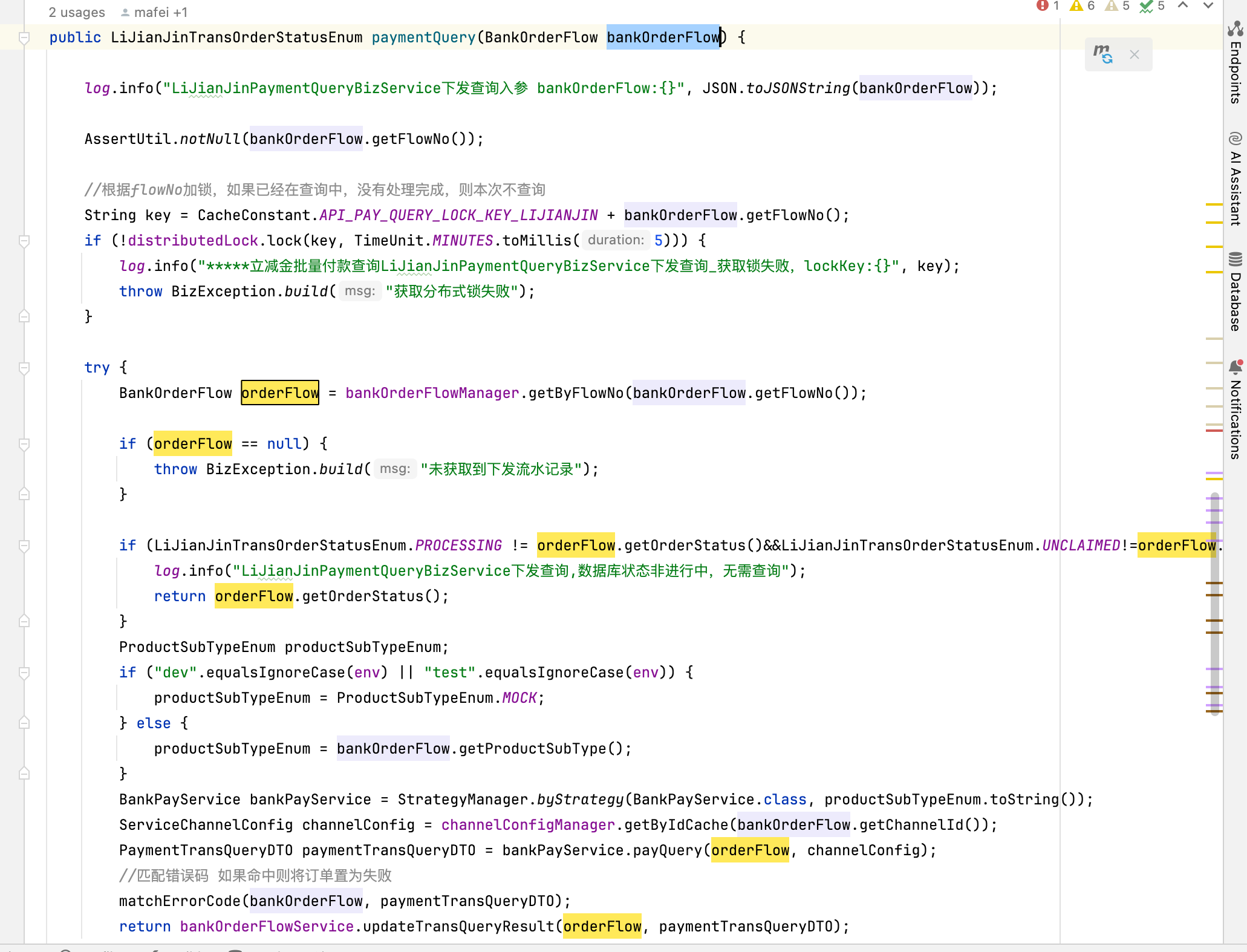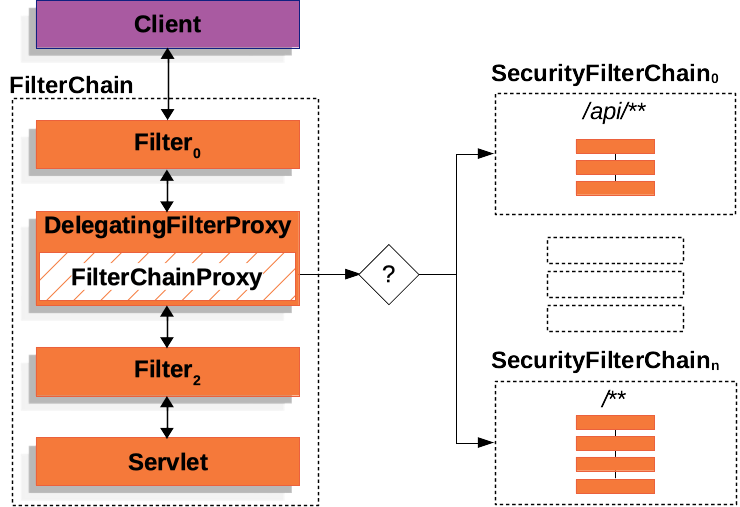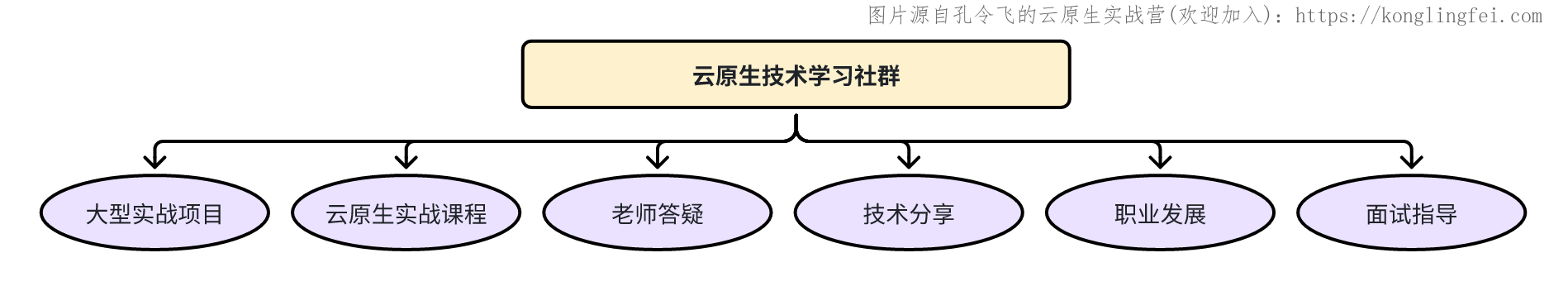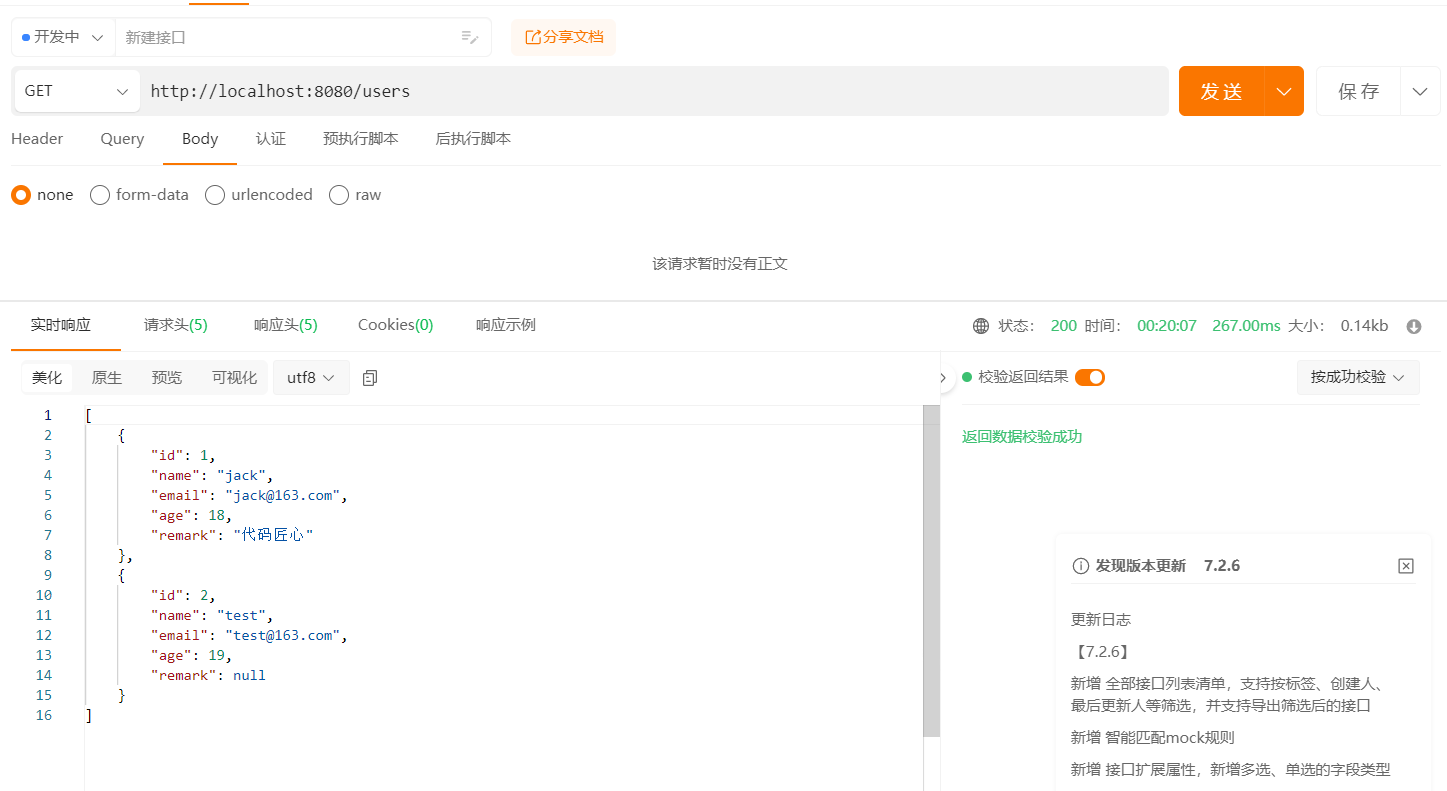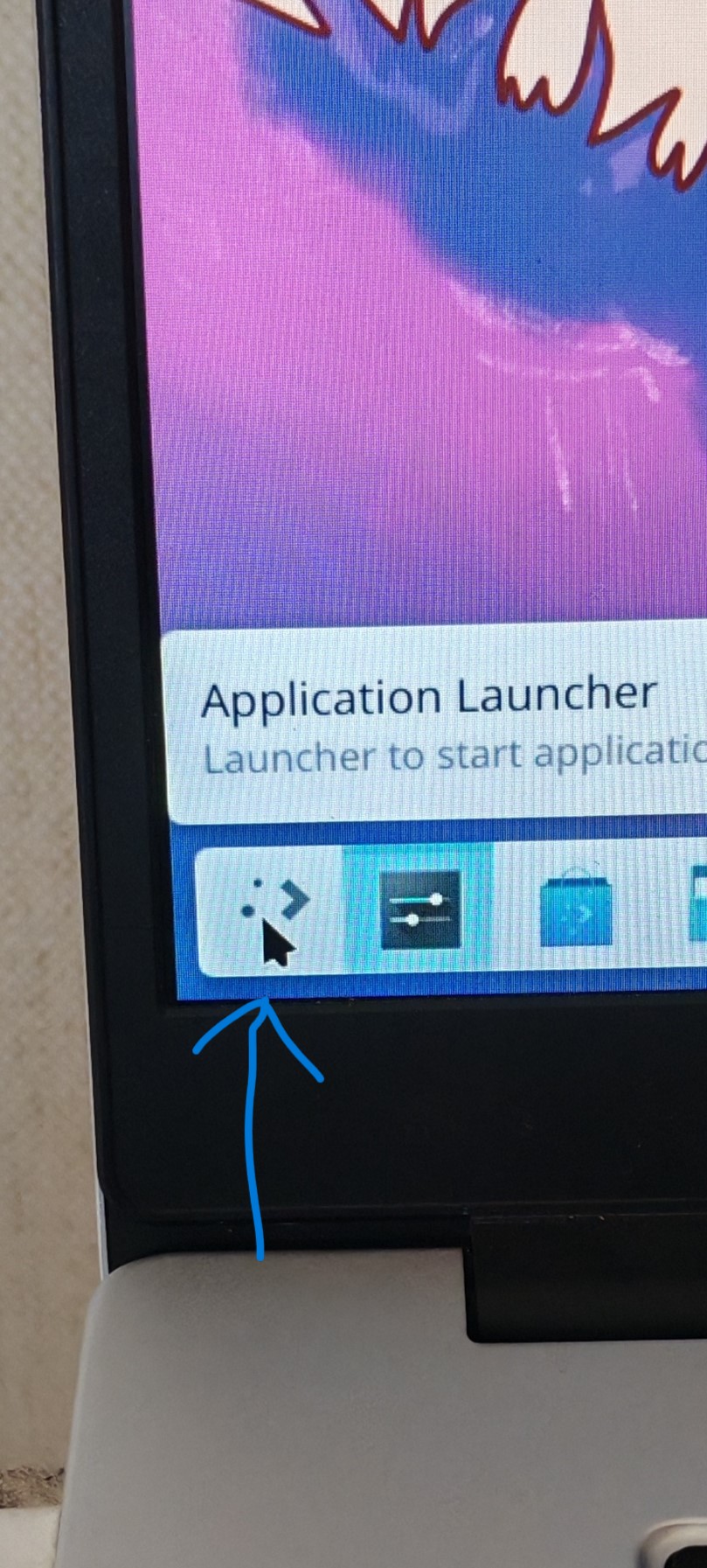文/轩先生
老家常有粉色的朝霞。我捏造那是亿万牡蛎凝结的梦,像一片烟尘,蒙蒙地笼罩着每一个亲眼看见它的人。沉默的广大的奇迹。
风刮过山谷叶梢的声音像极了喑哑的喇叭。少年的我以一种沉默的灰压着世界上每一个角落。我在湖岸艰难地向山顶爬去,风吹动着浮云往我们身后飘去,昏黑的天空就变成一条缓缓流动的河,点点星光是波光粼粼的水面。山下有个姑娘常对我说,只要一头扎进这条河里,我们就能游到月亮上去。后来她真的变成了嫦娥飞向了月亮,而留我一人在原地睹物思人。我要去荒山顶见她,那里离天顶只剩一丈不到的距离,黎明到来之际,那是我触碰她的唯一机会。
记忆里的童年,天总是灰蒙蒙的。秋天的时候,安插在城市四周的烟囱每到早操铃响的时候就开始向外吐出浓白色的烟雾。我总是揉着朦胧睡眼出发,推开锈迹斑斑的铁门,开始全新而重复的一天。 那时候的我很叛逆,想要逃离这里。起风了,我踮起脚尖站在小学操场边的最高的一个台阶上,张开双臂。我同桌站在最下面问:“嘿,你干嘛呢!”我轻蔑地回答说:“我要做一片落叶,我要飞!” 他跑上来,拉着我一阵狂笑,嘴里一直忍笑嘟囔着我刚刚的那句“我要飞!”我说:“我想逃走,越远越好。”偷偷告诉同桌这个幼稚又伟大的想法时,他捂着肚子笑得更开心了,头也没抬地说:“去哪啊,飞人,明天咱飞哪?”我没理他,继续着我的贴地飞行。
我不知道我能去哪,但我总想着去“那个地方”。在小孩们朴素的世界里,如果在这里过得不快乐,在那边,山海的那边,一定有“那个地方”。像动画片的主角,总能披荆斩棘一路,最终抵达幸福的彼岸。可无论谁都无法走出这弹丸小城,于是我们从小就开始了漫长的等到,期待下一个黎明到来之际,一切也许会生出一些微小的变化。
再长大了一点的时候,我开始苦苦思索。我开始知道宇宙和永恒是无限的,而我自己和一切人一样都是有限的。孤独原来才是人生一路的主色调,我也掉入这场没法醒来的梦。我不再迷信爱与浪漫,也久不再提起笔写作,只是上下班的时候经常会经过那座没有名字的荒山,我觉得它也好孤独。在路边踌躇良久,找了个没有鸡鸣的黎清晨,我要去山顶看看黎明 。我知道他们早就在等我了。
王小波说,破晓到来时,那是十万支金喇叭齐鸣。阳光穿过透明的空气,在暗蓝色的天空飞过。在黑暗尚未褪去的海面上燃烧着十万支蜡烛。
我们三人在荒山顶相遇时,一个人哭,一个人笑,还有一个人又哭又笑。这亿万牡蛎凝结的梦,神秘的梦幻的,烟雾般的,所有看见的人都会在这一时刻精神失常。沉默的广大的奇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