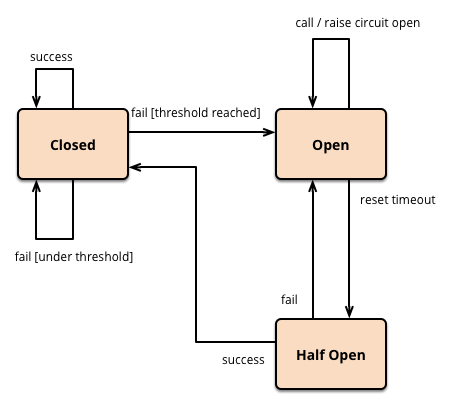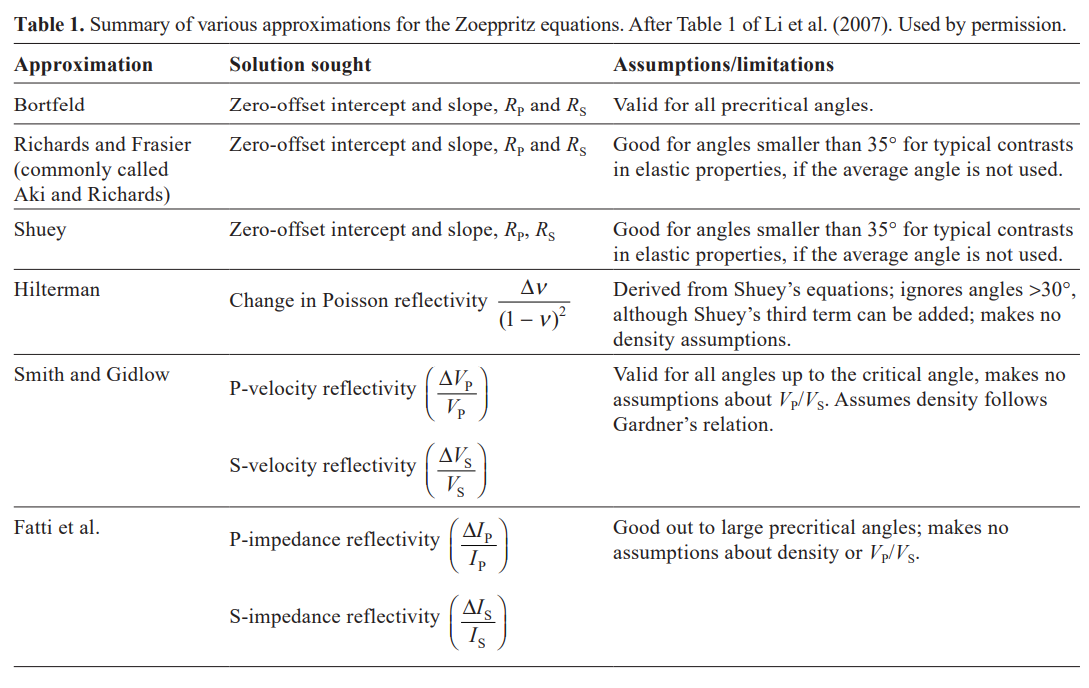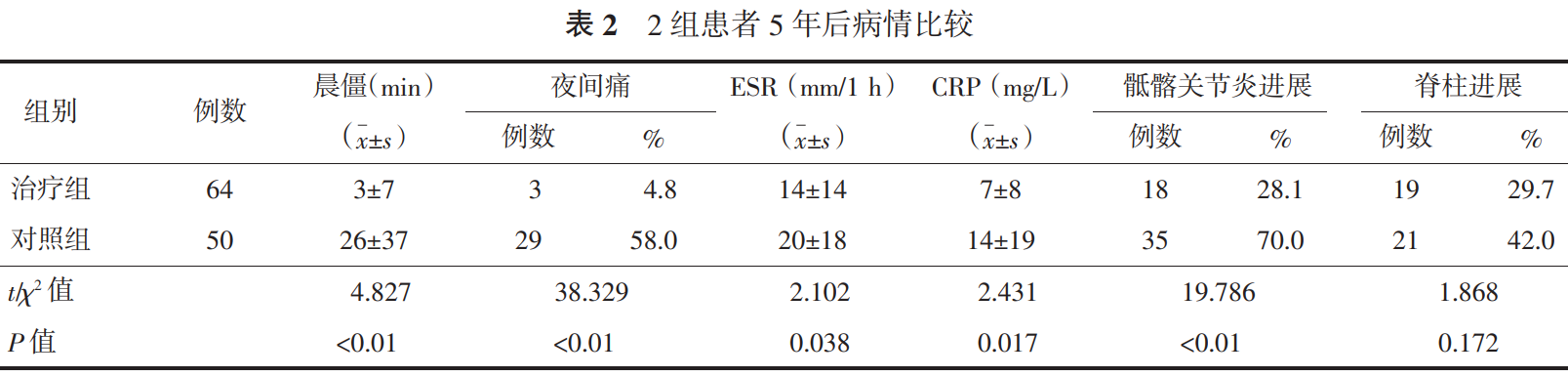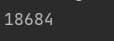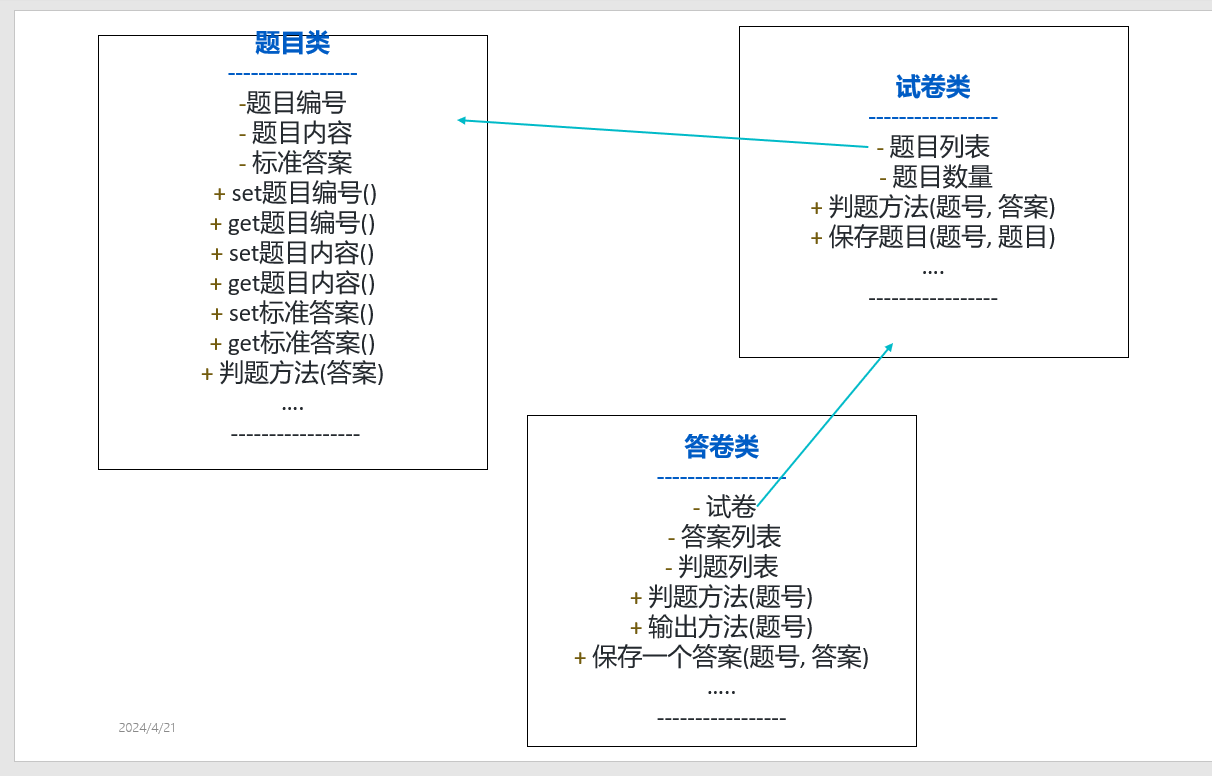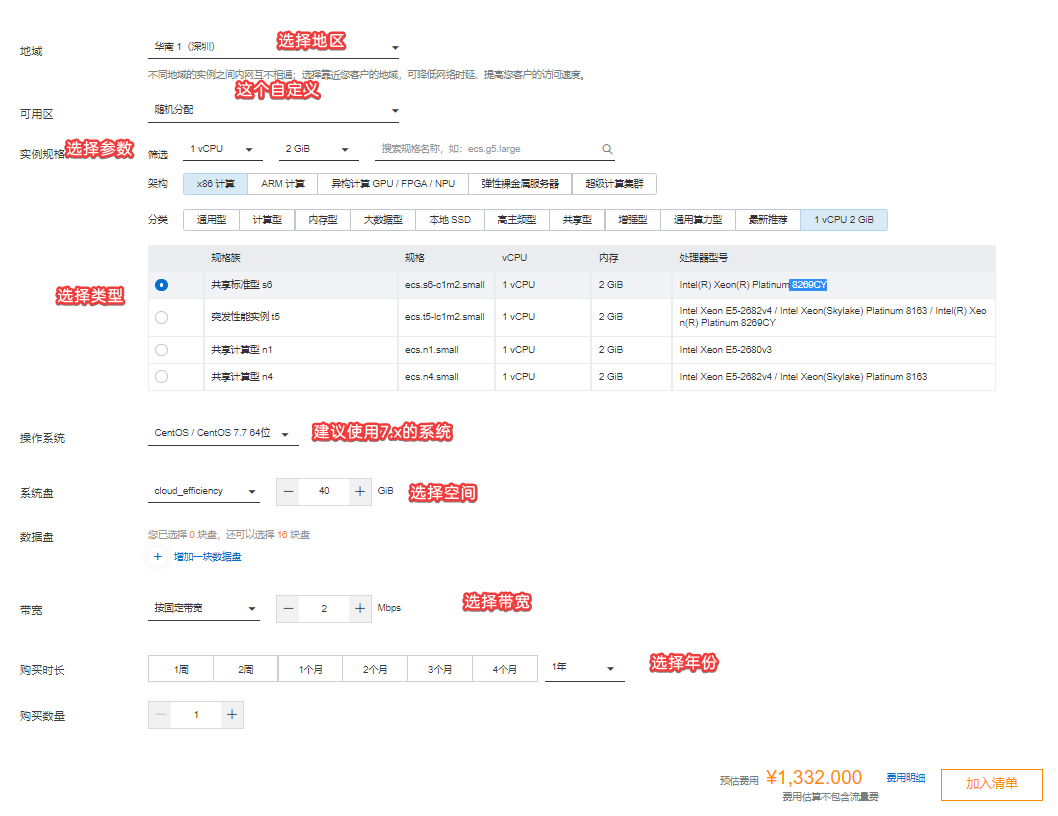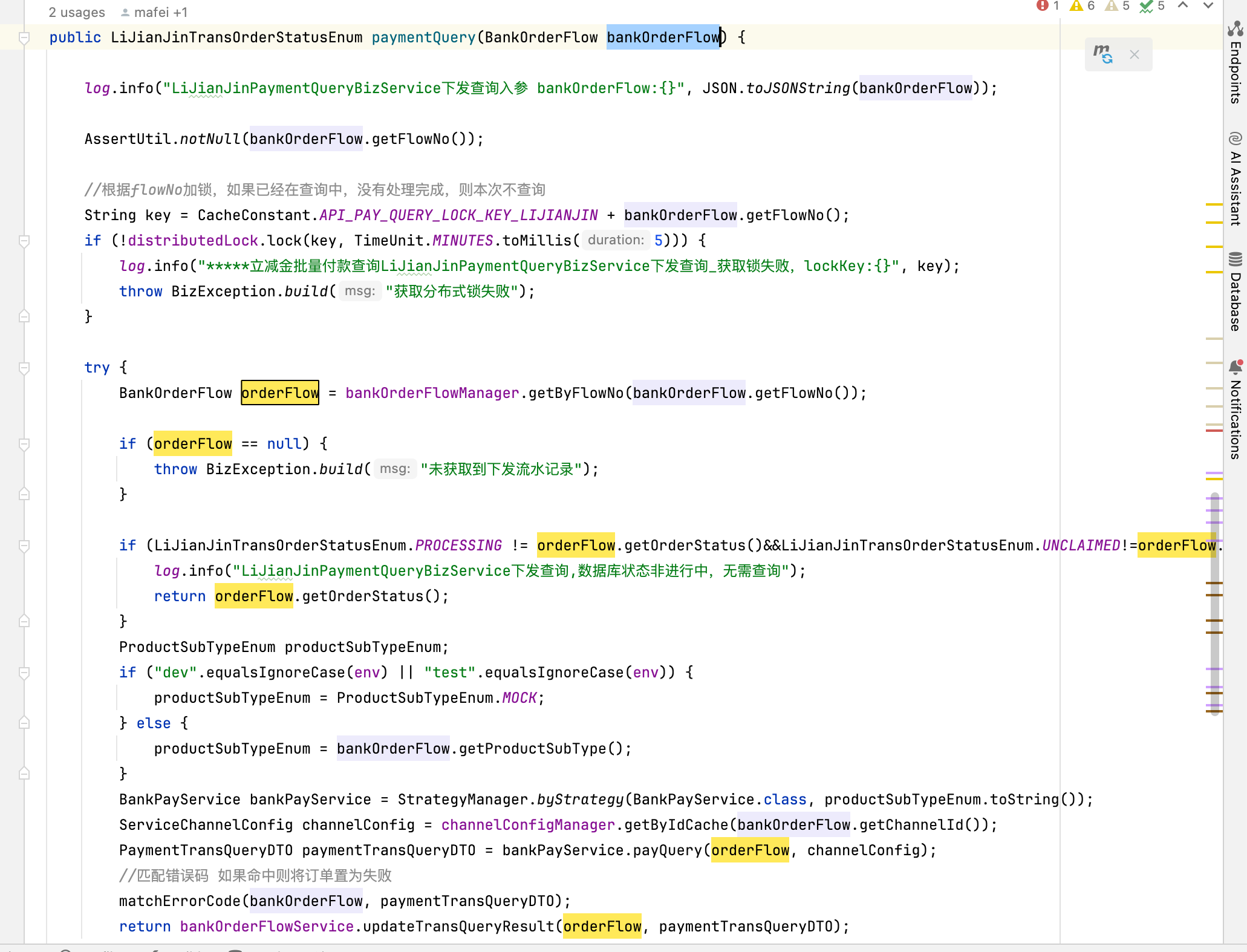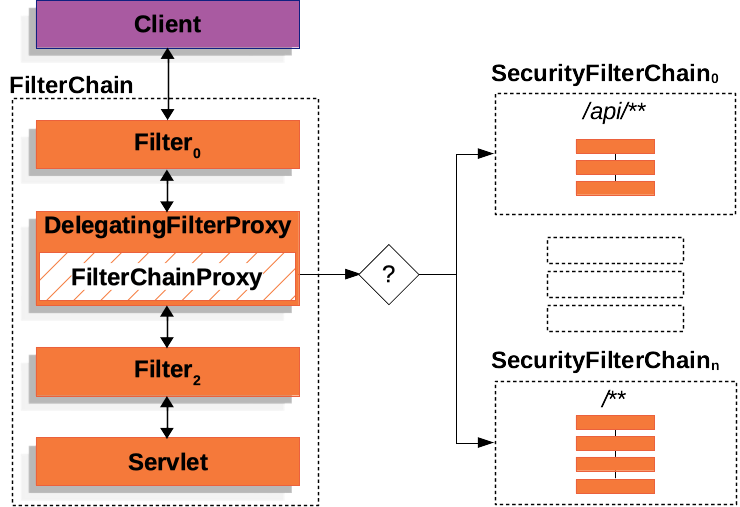一、普鲁士蓝
当他们的闪电战最终被盟军暴风雨般的轰炸扑灭,坦克的履带也被俄罗斯的冬天冻结,元首下令毁掉国境内所有有价值的东西,仅给盟军留下一片焦土。就在这一刻,帝国的最高统帅们尝到了一种十分不一样的东西;摆在他们面前的是彻彻底底的失败,他们给世界唤来的这派可怕的景象最终吓垮了他们自己,他们选择了一条最快的出路,咬碎了口中的氰化物胶囊,进而窒息在这种毒物的杏仁甜香里。
而最后仅剩的这点东西,盟军在半夜里把它撒进了文茨巴赫河。这条更像小溪的河流是他们在地图上随便选的,为的是避免后人将他最后的归宿当成朝圣目的地。但所有这些努力都是徒劳的:直到今天,全世界的收藏家还在交换着这最后一位纳粹大领导人、德国空军元帅、希特勒天然接班人的财产和遗物。二〇一六年六月,一个阿根廷人花了三千多欧元买进了这位帝国元帅的一条真丝内裤,几个月后,这个男人又为当初藏有戈林嚼碎的那支安瓶的铜锌发蜡筒付出了两万六千欧元。
铁、金、银、铜、锡、铅、磷、砷:十八世纪初的人类所知道的单质也就这么一小把。化学还没有从炼金术中分隔出来,而那一系列有着神秘名称的化合物,辉铋、矾、辰砂和汞合金等,就像培养液,孕育着各种幸福而始料未及的意外。
迪佩尔的灵药的成分之一最终产出的蓝色不仅装饰了梵高的《星夜》和北斋的《神奈川冲浪里》,也装点着普鲁士步兵的制服,仿佛在这种颜色的化学结构中包含着什么,将那位炼金术士的暴力、阴暗和污秽都继承了下来,再度唤醒。在一次又一次的实验里,迪佩尔肢解着活生生的动物,用它们的部件拼成了狰狞的奇美拉,试图用电击复活它们。而正是这些怪物激发了玛丽·雪莱的灵感,让她写下了她的名作《弗兰肯斯坦,或现代的普罗米修斯》。在书中,她曾发出过这样的警告,科学的盲目发展将是所有人类技艺中最可怕的。
在那儿,唯一重要的就是当下,而唯一的职责就是在战壕里尽我所能。但随后,我会回到指挥部,和电话绑在一起,那个可怜的女人对我说过的话就会回荡在我心里,而我一疲劳,电文中就会浮现出她的脸,叫我难过、痛苦。”
因战争延长而遭罪的人里就有个士官生,时年二十五岁。他真正想做的是艺术家,因而千方百计地逃避过兵役,直至一九一四年,警察来到慕尼黑施莱丝海姆街三十四号,把他揪了出来。面对坐牢的威胁,他去萨尔茨堡参加了体检,却被宣布为“不合格,体格过弱,无法携带武器”。而到了这一年的八月,成千上万人抑制不住对即将到来的战争的热情,都自愿报名参军了,我们这位年轻画师的态度也发生了急剧的转变:他给巴伐利亚的路德维希三世写了封亲笔信,请求作为奥地利人在军中服役。许可第二天就到了。
一九一八年十月十五日,正当他百无聊赖地等待着新命令时,英国人投放的芥子气让他瞬间失去了视力。战争的最后几周,他是在波美拉尼亚的帕瑟瓦尔克小镇里的一家医院度过的,只觉得眼睛变成了两块烧红的木炭。而当他听到德国战败、威廉二世签署退位诏书的消息时,他再度失明了,但这次失明和毒气造成的那次又是如此不同:“我眼前一片漆黑,我是踉踉跄跄摸索着回的屋,我一下扑到床铺上,把烧灼着的头颅埋进了枕头。”多年后,在兰茨贝格的一间牢房里,他是这样回忆的,他因领导了一次失败的政变而被指控为叛国。他在那里待了九个月,被仇恨所吞噬,为战胜国强加给他国家的接管条款以及将军们的懦弱而感到屈辱:他们选择了投降,而不愿战斗到只剩一个人。在狱中,他规划着他的复仇:他写了本关于他如何奋斗的书,并详细描绘了一个让德国屹立于所有国家之上的计划——如有必要,他准备亲手实现它。
此后,他从一个国家逃亡到另一个国家,希望能抵达巴勒斯坦,胸口被疼痛紧压着,因为他的血管已经无力向心脏输送足够的血液了。他是一九三四年死的,死在了巴塞尔,去世时手里还攥着扩张冠状动脉用的一瓶硝化甘油。他完全不知道,仅仅几年之后,他帮忙创造的那种杀虫剂会被纳粹用在毒气室里,从而杀掉了他同父异母的妹妹,他的妹夫和外甥,以及其他那么多的犹太人;他们都蜷缩着身子,肌肉僵硬,皮肤上是红色和绿色的斑块,他们的耳朵在流血,口吐白沫,年轻人把孩子和老人都压在了身下,他们在赤裸的尸堆上攀爬着,只想多呼吸几分钟或几秒,因为齐克隆B在从房顶的开口倒下来之后,是会积聚在地面附近的。随后,一待风扇把氰化物的雾气吹散,这些尸体就会被拖到几个巨大的炉子里去焚烧。他们的骨灰会被埋进万人坑,倒进河里、池塘里,或是撒在附近的田地里当作肥料。
二、史瓦西奇点
他算出的奇点无疑就属于这种情况:一个错误,一个怪东西,一个形而上的谵妄。
它不仅违背了常识,质疑了广义相对论的有效性,还威胁到了物理学的根基:在奇点上,连空间和时间这两个概念本身都失去了意义。卡尔想为他发现的这个谜团找到一个逻辑的出口,也许错误的根源就在于他自己的小聪明。因为没有哪颗恒星会是个完美的球形,完全不动,还不带任何电荷:这种反常现象都是萌生于他强加给世界的、不可能在现实中复制的理想化条件。所以,他的奇点,他告诉自己,虽然可怕,却只是个想象中的怪物。
然而,他又无法将它抛诸脑后。哪怕浸没在混乱的战争之中,奇点仍像一摊秽物,在他脑海中蔓延着,叠加在条条战壕织成的地狱之上;它出现在了战友们的弹伤里,倒在泥泞中的死马眼里,防毒面具玻璃的反射中。他的想象已经被他发现的那个东西给紧紧拽住了:他惊惶地意识到,但凡他的奇点存在,就会一直持续到宇宙的尽头。那些理想化条件把它变成了一个永恒之物,不增大也不缩小,而是永远保持原状。与其他所有事物都不一样的是,它不会随着时间而改变,且是双重不可逃脱的:在他创造的怪异的空间几何学中,奇点将同时位于时间的两端,不管你逃往的是最远的过去或未来,它永远都会在那里。
月亮飞快划过天空,就好像时间加速了。我的士兵都预备好了武器,正等待攻击的号令,可这怪异的天象对他们来说就像一个不祥之兆,我都能看到他们脸上的恐慌。
只有像圣人、疯子或神秘主义者那样,拥有一个整体的视野,才能破译宇宙组织的形式。
打小他的眼睛就离得很近,大耳朵、纽扣鼻、薄嘴唇、尖下巴。成年后,他长了一张宽阔的额头,而稀疏的头发则预示着他未能来得及发展的秃顶,他的眼神中满是智慧,而狡黠的微笑则躲藏在如尼采一般浓密的帝国式的胡子后面。
他读过《世界的和谐》,约翰尼斯·开普勒相信,每颗行星在环绕太阳时,都在演奏着一个旋律,那是星球的音乐,我们的耳朵是听不到的,但人脑可以破译它。
面对这些,他半开玩笑半当真地说,他牺牲了一个眼睛,为的是看得更远,就跟奥丁一样。
亚瑟·爱丁顿把他比作了游击队队长,因为“他的攻击都落在了最想象不到的地方,他智性的贪婪是没有边界的,所有的知识领域都被他涵盖在内了”。而同事们目睹了他在面对学术产出时的那种狂热,都很惊慌,劝他放慢节奏,生怕激励他的那把烈火最终也会将他燃烧殆尽。卡尔没理他们。他已经不满足于物理了。他渴望的是炼金术士所追求的那种知识,而催动他的,是连他自己也没法解释的一种怪异的紧迫感:“我常背叛天空,我的兴趣从未局限于月球之外、太空中的那些事物,而是顺着从那儿织起的那一条条线,滑向了人类灵魂更黑暗的区域,我们必须为那里送去科学的新光。”
打那时候起,他变了,甚至影响到了他做笔记的方式。他的字越来越小,最后都看不清了。在他的日记和寄给妻子的信中,爱国热诚让位给了对无意义的战争的苦涩的抱怨,随着他对同僚们的鄙视与日俱增,他的计算也越来越逼近奇点。最终抵达那里时,他已经想不了别的了:他彻底沉浸其中,对周围的一切心不在焉,以至于有次敌人都打过来了,他也没找掩体,一发迫击炮就在他头顶几米远的地方炸了,谁都不知道他是怎么活下来的。
不讲军事逻辑的暴行仍在不断发生着,往往都没法知道是哪一方的责任。而当史瓦西看到,他的一群手下正用远处一条吓得动都动不了、不停颤抖着的饿狗练习打靶时,他心中有什么东西崩塌了。他画的那些战友的日常,那些美景——随着部队的行进,它们变得越来越冷、越来越阴郁——都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整页整页炭笔的粗线和消失在纸页边缘的漆黑的螺旋。
我们已经来到了文明的最高点,那接着呢,就只能往下落了。
为了避免奇点的出现,他将算式写满了三大本本子,试图找到一条出路,或是他推理中的一个错误。而在最后一本本子上,他写下了他的结论:任何物体都可以生成奇点,只要它的物质被压缩到一个足够小的空间里。如果是太阳,三千米就够了,地球是八毫米,而普通人体则要达到0.000000000000000000000001厘米。
如果哪个假想的旅行者可以进入到这个稀薄区并且活下来的话,就能接收到未来的光与信息,见到还未发生过的事件。而他如果抵达了深渊中心,又没有被重力撕碎,就能见到两个重叠的景象同时投射在他头顶的一个小圈里,就跟万花筒一样:其中之一是以让人难以想象的速度激变着的宇宙的未来,而另一个,则是被冰结在某一瞬间的过去。
然而,怪事还不局限于那块区域的内部,奇点周围是有个界限的,一道屏障,把不归点给标记了出来。一旦越过那条线,无论你是什么(一整颗行星也好,一个亚原子微粒也好),都会被永远擒住,从宇宙中消失,仿佛掉进了个无底洞。
几十年后,这道边界被命名为史瓦西半径。
对聚在墓前的那一小群人,他是这么说的,尽管他们谁都猜不到,史瓦西被他最大的发现折磨到了怎样的程度,因为,连爱因斯坦都不明白,究竟发生了什么,他的方程才会变得如此奇怪,似乎“无限”才是它唯一的答案。
据卡尔说,这种级别的质量的集聚,最可怕的还不是它扰乱了空间,或对时间造成怪异的影响:真正可怕的是——他说——奇点也是个盲点,从根本上是不可知的。由于光也没法从那里逃脱,我们永远没法用肉眼看到它。用大脑去理解它也是不可能的,因为广义相对论的数学在奇点上失效了,物理学没有意义了,就这么简单。
如果说这样一种怪物也是物质可能所处的状态的话,史瓦西颤抖着问道,那在人类大脑中有没有相应的东西呢?意志的充分集中,数百万人受制于同一个目的,思想被压紧在同一个精神空间里,会不会生成一个类似于奇点的东西?他不仅相信这是可能的,而且正在他的祖国发生着。柯朗试图安抚他,说,他担心的那种悲剧,自己没有看到任何的迹象,而且不可能有比他们置身其中的那场战争更糟糕的了。他还提醒史瓦西说,相比任何数学谜题,人类的心灵是个更大的谜,把物理学思想投射到这么远的心理学领域,是不明智的。但史瓦西却无法自拔。他喋喋不休着,一个足以吞掉整个世界的黑色太阳正从地平线上探出头来,同时哀叹,我们已经无能为力。因为他的奇点是不会发出警告的。那个过去就回不来了、只能束手就擒的不归点,没有任何的标志。越过它的人就没有希望了,他的命运已经被不可逆转地划定了,所有可能的轨迹都直直地指向了奇点。那这样一道界限,史瓦西问道,两眼充血,我们怎么知道自己有没有越过呢?
柯朗返回了德国。当天下午,史瓦西死了。
为驱散卡尔唤来的那个魔鬼付出最多努力的正是他的朋友,阿尔伯特·爱因斯坦。一九三九年,他发表了一篇文章,名为《论多引力质量的球对称静止系统》,解释了为什么不可能存在史瓦西的奇点。“奇点不会出现,原因很简单,物质是不可以被随意聚拢的,否则的话,组成它的微粒就要达到光速了。”凭借着他一贯的聪明才智,爱因斯坦用他理论内在的逻辑给时空裂隙打上了补丁,把宇宙从灾难性的引力坍缩中解救了出来。
然而,二十世纪最伟大的物理学家算错了。
它可以把空间像纸一样揉皱了,像熄灭烛火一样熄灭时间,任何物理力或自然法则都不能让它们幸免。
三、心之心
他痴迷空间,他最独到之处就是把“点”的概念给扩展了。在格罗滕迪克的注视下,卑微的点不再是没有面积的一个位置,而是从内部膨出了复杂的结构。别人眼里没有长宽高、没有大小的一个地方,亚历山大看到的是一整个宇宙。自欧几里得以降就再没有人提出过这么大胆的设想。
他是个优秀的拳击手,狂热地爱好巴赫和贝多芬晚期的四重奏。他热爱大自然,崇尚橄榄树的“谦逊与长寿,充满阳光与生命力”。而在包括数学在内的世间万物中,他真正喜欢的还是写,以至于不让他写下来的话,他都没办法思考。他的狂热还体现在,他有好些手稿,笔都穿透了纸张。他会在本子里写下那些方程,然后一遍遍地描它们,描到都看不清了,单纯因为喜欢石墨搔挠纸张的那种生理上的快感。
在挫败与沮丧中,托姆发展出了他的突变论,描述了任何动态系统——无论是一条河、一处构造断层或是人类的心灵——在失去平衡的状态下,会以哪七种方式发生突然的崩溃,从而陷入无序和混乱。
“激励着我的不是野心或对权力的渴望,而是我灵敏地感觉到了某种巨大的、非常真实同时又非常微妙的东西。”格罗滕迪克还在继续把他的抽象推向愈发极端的界限,才刚攻克一个领域,他已在预备着扩张它的疆界。他研究的巅峰便是“动机”的概念:这是一束光,足以照映出一个数学对象的所有可能的化身。“心之心”,他是这样称呼位于数学宇宙中心的这个实体的,而关于它,我们所认识到的不过是它最遥远的闪烁。
连他最亲密的合作者都觉得,他走得太远了。格罗滕迪克想用只手抓住太阳,掘出那个能把无数没有明显关系的理论连结到一起的秘密的根系。有人告诉他,这是不可能做到的,与其说这是科研项目,它更像自大狂式的谵妄。亚历山大没有听。他已经挖得这么深了,他的思想已经触及到了那个深渊。
最终结果这个星球的不是政客,他说,而是像他们一样的科学界人士,他们正“像梦游者一样走向末日”。
在接下来的几年里,他舍弃了家庭,抛弃了朋友,遗弃了同事,逃离了这个世界。
“搞数学就像做爱一样。”格罗滕迪克写道。他的性冲动完全可以和他的精神追求相匹敌。他一生引诱过许多男人和女人,他和妻子米雷耶·杜福尔生了三个孩子,而婚外还有两个。
她几乎无法控制自己的激动,接着就告诉他,他年轻时提出的一个重要猜想被证明了。格罗滕迪克淡淡地笑了笑,说道,他对数学已经完全没有兴趣了。
四、当我们不再理解世界
把诸如位置、速度、动量等的经典物理概念用到亚原子粒子上完全是无稽之谈,自然界的这一面需要新的语言。
海滨长廊的店家就像被巨大的火炎风暴刮过,成了烧焦的废墟。人们在它周围游逛,皮肤上都带着灼伤的痕迹,而那团火焰,只有他才能看见。孩子们奔跑着,顶着冒火的头发;情侣们像焚尸堆的柴火一样燃烧着,齐声大笑,纠缠着的手臂好似火舌,从他们体内钻了出来,伸向天空。海森堡加快了步伐,试图控制住双腿的颤抖,而就在此时,一声巨大的炸响撼动了他的鼓膜,一道光闪穿透云层,在他脑中钻出了一个洞。他奔向旅馆,实实在在地被光闪瞎了双眼,偏头痛也发作了。他只能强忍着恶心和从眉心蔓延至耳朵的疼痛,脑袋像被劈成了两半。当他终于能够爬上楼去时,他昏倒在床上,因发烧而颤抖着。
天上没有星星,只有被月亮照亮的云。
玻尔努力尝试了,也没能解开海森堡创造矩阵时古怪的逻辑,可他非常清楚,这个年轻人发现的是一种极其根本的东西。他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通知爱因斯坦,“海森堡的新文章马上就要发表了,我看完一片茫然。很像是哪个神秘主义者写的,但无疑结果是对的,而且很有深度”。
在他那篇论文里,爱因斯坦看到了物理学的一条新路的起始:“他掀开了大幕的一角,量子世界是我们这代人最大的困境了,而这是其中的第一缕微光。”
由于暴雨将至,要塞周围的铁丝网尖端堆积了静电,就冒出了等离子的“火苗”。薛定谔被彻底迷住了,他望着那些小小的蓝色光点,直到最后一处消失。终其一生,他一直都在怀念那串奇异的冷光。
从他感受到山间稀薄空气的第一分钟起,就有什么在他想象中成形了,而他知道,任何的分心,哪怕微乎其微,都有可能消解这种魔力。
他对面坐着的老妇,他最先注意到的是她细长的手指,那显然是由数个世纪的财富和特权雕琢而成的,而在她端着的茶杯背后,那张脸的下半部分已经完完全全被结核杆菌给腐蚀了。
鬼魂一个接着一个,像生与死的幻觉之海中的浪。生命里什么也没有,除了物质与精神的各种形式的升降,而不可探知的真实永存。每个造物中都沉睡着无尽的、不为人知的隐秘的智慧,可它注定是要醒来的,撕碎感官思维的那张轻薄的网,搅碎它的肉蛹,征服时间和空间。
马克思·普朗克是第一个提出量子存在的人,他写信给薛定谔说,他读到那些论文时,是怀着一种“无比喜悦的心情,就像一个孩子,被一道谜题难住了好多年,终于听说了它的答案。”保罗·狄拉克就更过分了:这个古怪的、拥有传奇数学能力的英国天才说,奥地利人的方程几乎涵盖了当时已知的所有物理学,以及化学——至少可以说基本是这样。薛定谔已经触到了天堂。
这年头啊,没人有时间享受永恒。也就只有小孩儿,小孩儿和醉汉,您这样的正经人肯定不行,你们就要改变世界了,是不是啊,教授?
他没告诉玻尔死在他脚下的婴儿的事,还有在森林里围着他的那成千上万的人影,他们在那道致盲的闪光中被瞬间碳化了,仿佛是想警告他什么。
上帝不跟宇宙玩骰子!
海森堡二十五岁时被莱比锡大学任命为教授,他也是德国历史上最年轻的教授。
一九三二年,他因为创造了量子力学获得诺贝尔奖,而一九三九年时,纳粹政府命令他对核弹的制造开展可行性研究;两年后,他得出结论,此类武器是德国或任何一个敌国都无法企及的,至少是在大战中;当他听到核弹在广岛上空爆炸的消息时,他几乎不敢相信。海森堡一生中还在继续发展各式各样挑战常识的想法,他被认为是二十世纪最重要的物理学家之一。
迄今为止,他的不确定性原理经受住了所有的考验。
总结
看这本书的时候,我会时常在想一个贴吧的段子“是真的,我就是那个XX”。其中的一些情节让人感觉作者就像是长在书中人物脸上的摄像头一样。这种对于细节的描写让读者感觉到呼吸的历史,描绘出一个符合大众想象的历史人物形象。但是读完这本书也需要思考一下,书中的很多情节都是虚构的,完完全全是为了刻画人物性格而做的描述,应该分清其中的虚虚实实,坚定自己心中的哈姆雷特。